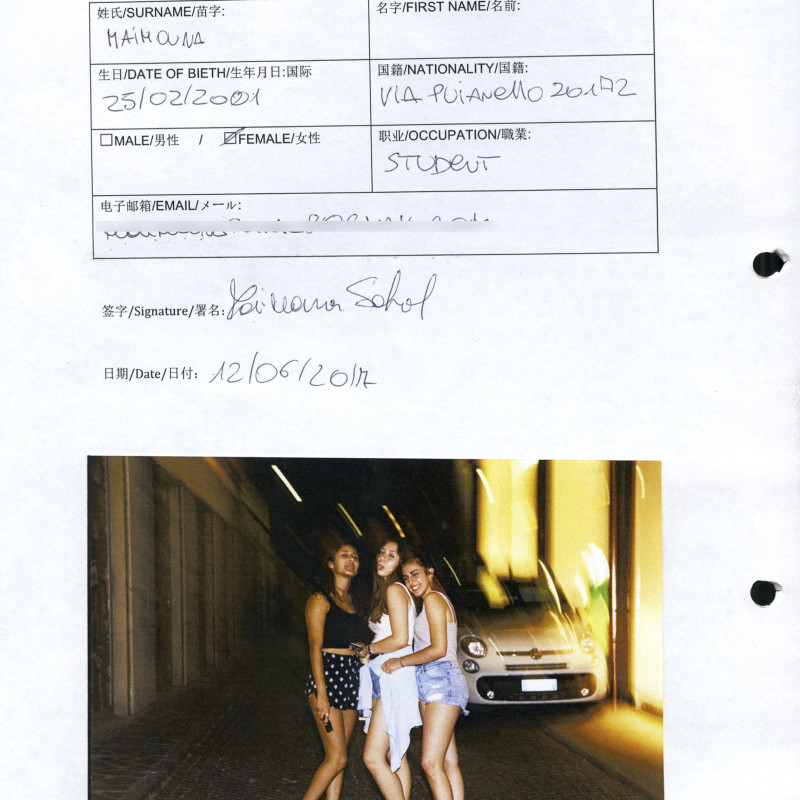主办: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
艺术总监:荣荣&映里
策展人:沈宸
开幕:2018年6月9日下午4时
参展艺术家名单 (按姓氏拼音首字母排序)
病女、蔡东东、陈萧伊、陈哲、程新皓、储楚、戴建勇、杜艳芳、冯立、黄京、黄晓亮、蒋鹏奕、九口走召、李俊、良秀、林志鹏(编号223)、刘张铂泷、卢彦鹏、罗洋、骆丹、木格、丘、任航、沈凌昊、孙彦初、塔可、王淋、王拓、王岩、魏壁、许力静、杨圆圆、张晋、张克纯、张文心、张晓、张之洲、朱岚清
十年来,三影堂摄影奖致力于从不断涌现的摄影艺术新潮流中,选取具有独立精神和艺术潜质的艺术家及作品,考查、梳理和研究中国当代摄影、将中国当代的新锐摄影介绍给广大公众,进而推动中国当代摄影的发展。三影堂摄影奖就像是一扇窗,让世界更好地了解到当下的中国摄影的多样性以及新生力量。
以2008年4位年轻摄影艺术家参加的群展“外象”为契机,三影堂自2008年开始向社会公众发布公告,进行三影堂摄影奖评选及展览作品的征集。在三影堂各合作机构及社会各界的支持下,2008-2009年度的评选和展览活动得到了众多的摄影艺术家的积极响应,并以“临点”为题,三影堂成功地举办了首届摄影奖展览。历经“临点”、“交汇”、“万相”、“跨越”、“实相”、“无相”、“离相”、“无量”、“寓言”、“起承”,三影堂摄影奖在这十年里吸引了全球近5000位华人摄影师及艺术家投稿参赛,共发掘了超过200位青年摄影师及艺术家入围参展。
在这十年中,三影堂邀请到超过30位来自业界最重要美术馆(如伦敦泰特现代美 术馆、纽约现代艺术美术馆、洛杉矶盖蒂美术馆等) 的总监、策展人(西蒙·贝克、昆丁·巴耶克等)以及最重要的摄影艺术家(希拉·贝歇、坎迪达·赫弗、 托马斯·鲁夫等)来到三影堂,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是通过参与这个奖项的契机第一次来到中国,共同参与并见证了一次次中国新一代摄影新秀的诞生。
值此之际,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策划“十方:三影堂摄影奖十周年特展”,遴选过往十届中最具代表性的青年艺术家,展示他们的全新创作。此外,我们还特邀到凯伦·史密斯、顾铮、饭泽耕太郎、蔡萌等国际国内专家为本次展览画册撰写学术文章,并将在展览期间邀请业内专家、艺术家、相关人士开展系列研讨会议。
本次“十方:三影堂摄影奖十周年特展”以一种非编年史的架构展现当下中国青年创作群体于过去十年来进行的摄影艺术多元实践,亦是对三影堂摄影奖十年来工作的回顾和总结。同时,邀请观众以一种超越对摄影静态定义的理解去沉思作品带给我们的视觉感受;也提供一个现场,使观众去理解中国摄影师和艺术家们通过“摄影”这一媒介所进行的工作,前行的方向,推动的边界。
点击查看开幕回顾
▷ 为“十方:三影堂摄影奖十周年特展”而作
沈宸
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策展人
偏居北京五环外一隅的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是由中国当代著名的摄影艺术家荣荣和他的妻子、日本著名摄影艺术家映里于 2007 年 6 月共同创办的国内首家专注于当代摄影艺术的民间艺术机构。有感于当时国内缺少面向青年艺术创作群体的摄影推广和展示平台,荣荣和映里发起了三影堂摄影奖这一“旨在在不断涌现的摄影艺术新潮流中,选取具有独立精神和艺术潜质的艺术家及作品,考查、梳理和研究中国当代摄影,将中国当代的新锐摄影介绍给广大公众,进而推动中国当代摄影的发展”的奖项平台。
以 2008 年 4 位年轻摄影艺术家(阿斗、蔡东东、卢彦鹏、丘)参加的群展“外象”为契机,三影堂从2008 年开始向社会公众发布公告,进行三影堂摄影奖评选及展览稿件的征集。在三影堂各合作机构及社会各界的支持下,2008—2009 年度的评选和展览活动得到了众多的摄影艺术家的积极响应,并以“临点” 为题,三影堂成功地举办了首届摄影奖展览。历经“临点”“交汇”“万相”“跨越”“实相”“无相”“离相”“无量”“寓言”“起承”,三影堂摄影奖在这十年里,共发掘了超过 200 位摄影师及艺术家。 历经十年,曾经的参展艺术家们已在相关领域中取得了各自的长远发展。此次“十方:三影堂摄影奖十周年特展”,邀请曾参与三影堂摄影奖并仍活跃于中国当代摄影和当代艺术中的青年艺术家,重新集结并展现他们各自近期的创作与实践。接下来,本文将通过部分例子,希望以不同的视角,为观众 / 读者提供进入这些艺术家所进行的工作的切口,但其目的并非要类型化和标签化各位艺术家的创作。实际上,很多艺术家的实践对摄影触及的问题从多个面向上均有所涉及与互指。
正如摄影的英文单词“Photography”的词源所指示的,摄影首要是关于光的技术和艺术。若以 1839 年具有广泛实用意义的达盖尔银版摄影法为开端,摄影的显影和感光材料于一百多年间已历经各种发展和变化。尤以理查德·利奇·马多克斯发明的明胶银盐工艺、Kodak 公司发明的彩色胶片为代表,塑造了前数字时代的主要摄影工业形态。在当下,数字摄影(尤其在智能手机的推波助澜之下)已成功地取代传统胶片摄影成为主流。但这一情况,反而为部分艺术家重新审视模拟摄影遗留的问题和蕴藏的潜能提供了契机。沈凌昊的《剩余物》系列中展现的抽象图像,是艺术家在扫描过去拍摄的底片过程中发现的一些冲印失误以及无法被归类的图像。本身为留下事物形象和记忆被发明的摄影,此时却成为无法被辨明的图像以及无法被追溯的记忆,这些没有明确意涵所指的图像成了失效的产物,亦成为“时间的剩余物”。而陈萧伊的《Recurrence》则从胶片的二维图像空间轻轻逃逸,仍以胶片为物质平面,却同时间与尘埃进行了合谋。这些漆黑的胶片并未被用来完成自己感光的使命,反而日积月累地拥抱了灰尘留下的痕迹,在艺术家扫描后点缀出一方幻如宇宙的真假时空。孙彦初的《光影》则从胶片的平面中全然跳脱出来,意识到胶片是作为形塑光影的“中间物”。这里的中间物既是首次“为光留影”的必然产物,也是再次“为光投影”的必要条件。通过精心控制光的入射位置及角度,以及摆弄塑造半透明胶片的形态,艺术家重又使得墙上的投射还原了胶片上的光影印相。
与上面几位探讨了胶片的物质性及相关问题的艺术家不同,还有一些艺术家则从作为物质实体及材料的摄影照片入手,有意识地对这一媒介的本质属性进行了利用和解构。蔡东东以冲洗的旧照以及从二手市场淘取的老照片为基础,提取出那些看似无用的“废片”,以原作为“画布”,以刻刀与手指为“笔”对其加以再创作。通过“折磨”、刺穿、形变、移除照片中的部分图像及附属信息,配合以具有“误导”性的标题,使这些几乎成为雕塑的照片原本所负累的信息被改写,并被重塑为新的意义空间。在此次展出的《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度过》(《向晚六章》第一章第二节)中,陈哲将一系列自己拍摄的照片与各有所指的挪用图像并置。艺术家对来源不同的照片采用了不同的特定装裱形态,却并非意在把玩不同的材料,而是为这些不同的物质赋予精神联结;此外,四组黑色的金属架,好似巨大的相框又如同珍物柜,含蓄地为观者提供了体验“黄昏”时四种心理状态的入口,并使得呈现的对象不再是某一幅特定的图像,而是一整组图像内部自由而有序的流动关系。
归功于摄影形象化刻记外部世界的能力,摄影从发明之初便成为人类用以记录和讲述人类文化记忆的重要工具。然而以单帧为基本单位的摄影,其所谓的“纪实”或“叙事”能力实际上又充满了极大的含混和不确定性,极易在图像实际使用者赋予的杂讯和上下文的影响下产生“歧义”。基于此种特点,展览中的部分艺术家创作了基于“事实”与“虚构”之间的摄影叙事,并重新审视了关于摄影的纪实传统。在《东岛博物志》和《大连幻景》两则基于地点并以历史往事为出发点的半虚构艺术项目中,艺术家程新皓和杨圆圆分别对“博物学背后的知识逻辑”以及“何为故乡” 两个话题进行了探讨。尽管两组作品背后所试图发问的对象极为不同,但相似地,艺术家们通过使用文本、声音、录像、装置乃至行为表演,使摄影照片成为整个叙事结构中的其中一环,通过材料间的互文策略,对他们意在触及的艰深问题进行了回应。与上述艺术家采取的策略有所不同,张晓在作品《萌萌》中虚构了一个关于真实存在于艺术家故乡烟台的名为“萌萌”的青年形象。在这组作品中,张晓将自己拍摄的照片,以及挪用自萌萌拍摄并发布在手机社交网络上(从画面质量到内容都极为粗粝)的照片、文字、视频、网络流行热图、段子等混淆在一起,时而塑造两者的对话,时而重合两位“作者”的身份,以半自传体的方式讲述了属于这个大时代之下的小城 a 故事。
与摄影的记录能力相关,(作为行为的)摄影及(作为行为产物的)照片常常同所谓“记忆”“回忆”等概念相连,并以拍摄者和被拍摄者的关系为基础,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存在的证据。在参展的艺术家中,病女、戴建勇、林志鹏以及良秀等,从爱情、亲情、友情以及自我关系等不同向度上,展露出摄影在处理个体、主观、私密等话题中所具备的惊人潜能。在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中,摄影不仅成为记录关系的媒介,更成为推进关系发展的催化剂。有趣的是,展览中的另一些艺术家则从相反的角度,对摄影与“记忆”“关系”等话题进行了反思和解构。九口走召的《Proof》系列使用了热敏纸作为承载照片的媒介。这种常用于打印购物小票的纸张会在温度的变化中,缓慢又在某种意义上迅速地(与专门用于照片打印的纸张相比)使附着其上的信息(图像或文字)消失。艺术家使用这一日常材料,直截了当地对摄影作为记忆证据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许力静在《W&W AM I》中,邀请熟人乃至陌生人取代摄影师本人按下照相机快门,并让他们签署包含了姓名、性别、国籍、职业、邮箱等信息在内的图像使用协议。在这一行为中,艺术家、采访对象乃至观众之间都塑造起了某种关联并使彼此之间产生了某种程度的进一步了解。但我们也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去质疑这种以拍摄建构起的临时性关系及其联结能够到达的深度。张文心的《内存腐蚀》则将自己于过往旅程中拍摄的照片作为贴图,通过 3D 软件对其中的场景进行还原式建模,并使虚拟人取代本人回溯了其记忆中的行为,从而将真实世界中的时间体验挪移到虚构的人物身上。然而一旦剥离这些残留了现实世界物质痕迹的照片,虚拟人的行为亦将陷入虚无当中。于此,我们或许可以发问,到底是我们以照片保留了记忆,还是记忆通过照片塑造了我们?
在记录个体的私密记忆之外,摄影师也常常介入全球化图景之下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等议题的讨论当中。但全球化作为一种将一切事物标准化的力量,也使得不同国别、区域的文化内涵及独特性受到威胁。由此,一种基于“本土化”或“在地性”的创作和争辩也应运而生。尤其是在此次展览中,我们看到了中国摄影师们一系列“摄影中国”的实践。实践的方式之一,是直面中国人的生活日常:冯立和黄晓亮的作品都以当下剧烈变迁的中国都市为背景。前者游击于成都的大街小巷,以闪光化作投枪,每每径直刺穿现实的荒诞,给人呈现淋漓的“血色”;后者隐匿在无名的街头巷陌,守候于华灯与氤氲初现之时,静看芸芸人间烟火。实践的方式之二,是遨游当下的中国:“回家” 之后,木格整装出发,“延墙而行”,远离了与现代化赛跑的大城市,以苦行僧的方式走过 128658 公里的路程。在他的大画幅照片中,苍凉的北国风光成为被时代遗忘的“肖像”,满脸皱纹的面容成为藏匿失
落记忆的“风景”。实践的方式之三,是重思独属中国人的精神向度:塔可在继《诗山河考》和《碑碌——黄易计划》之后,将目光和兴趣转向对道教中“连接人类世界和神仙居所”的“洞天”概念的研究。以对古典文籍的研读为前提,塔可开始了一段参访中国历史中洞天福地以及人造洞穴的行旅,并以他一贯诗意的黑白摄影语言,探讨我们的现实世界同神话、历史时空之间的复杂关系。
“十方:三影堂摄影奖十周年特展”,试图以一种非编年史的架构展现当下中国青年创作群体于过去十年来进行的摄影艺术多元实践,亦是对三影堂摄影奖十年来工作的回顾和总结。然而展览并非想要也无意去塑造一个事无巨细地涵盖中国当代摄影实践的所谓全景样貌,而是以 38 个个体的视角,去展现这些摄影师和艺术家各自的成长和他们自身的关切。同时,邀请观众以一种超越对摄影静态定义的理解去沉思作品带给我们的视觉感受;也提供一个现场,使观众去理解中国摄影师和艺术家们通过摄影这一媒介所进行的工作、前行的方向、推动的边界。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一奖项面向的是中国的摄影艺术创作群体,但其始终秉持着学术性、公平性、国际性的原则。每一届入围艺术家及最终大奖得主的诞生都是在世界各国顶级美术馆的总监、策展人、艺术史家以及领域内最重要的摄影艺术家的共同投票下产生的。因而,三影堂摄影奖也可说是世界艺术界、摄影界对于中国摄影发展的共同见证与希冀。
从本质上来讲,艺术事关求知欲、好奇心,是对美的向往,是同世界构筑连接的冲动,是对陈规旧俗的质疑和挑战,以及对人性的审问和自我的追索。若此,艺术与摄影就不会终结,我们对未来还可有所期待。正如展览题目“十方”所暗示的,这些艺术家来自中国乃至世界各地,他们注目的世界是关于过去、当下与未来的。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亦将秉持初心,与各方一道,继续支持中国青年摄影师和艺术家群体的创作和发展。让我们共同见证下一个十年的到来!
▷ 好的评奖是一种制度生产
顾铮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摄影评论家\策展人
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
如果把中国当代摄影的发展放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中加以认识的话,其发展不只是体现在摄影本身的从观念到手法的变化与发展,更重要是一种由于摄影本身的发展所触发的、所促成的对于艺术制度的发展的各种探索。至于当代摄影与艺术制度的关系的思考与研究,至今仍然相对缺乏。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思考与研究不重要甚至可以忽略。这种缺乏,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对中国当代摄影的历史与发展的更深入的研究,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于艺术制度创新的促进。
由荣荣与映里创设的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对中国当代摄影的发展,尤其是在艺术制度创新方面的贡献有目共睹。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作为一个艺术交流的平台,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摄影人士的深入交流,也为中国的摄影家与艺术家的展现才华提供了助力与舞台。这个舞台,由于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创设的“三影堂摄影奖”评奖活动的举办而更加有声有色。因为有了这个奖项以及相应的其他一些奖项,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就不仅仅是一个作为硬件的展览空间,而更是一个通过评奖等活动来生产内容、来展示中国当代摄影的现状,制造参评者与评委和观众的交流,以及提示某种变化与发展端倪的一个始终充满活力的创造现场。最终,这样的努力以及努力之中的各种创新,就理所当然地转化为一种对于中国当代摄影发展的制度性的引领。
身为曾经参加过“三影堂摄影奖”评奖活动的评委,可以发现这个评奖过程中的许多环节与细节在中国是首创的。比如,经过初评评选出来的摄影家与艺术家们,可以在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的开阔展厅里,按照自己的展览布置设想,在展厅里精心布置自己的作品,以求最好的呈现效果。然后,他们与评委在自己的作品面前展开平等、直接的交流,充分阐述自己的创作观念,与评委共享由自己的作品以及由自己创造的展览空间所挥发出来的各自作品的独特气息与魅力。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陈述,来尝试与评委沟通,而不是如许多评奖那样,参评者只是接受评委单方面的评判而自己只是被动送审。这是一个充分考虑了参评者的主体性如何体现的制度设计,也体现了对于参评者的尊重,从根本上体现了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对于摄影艺术的尊重。试想,那些出于各种无奈只是在电脑荧屏上稍纵即逝的影像,其所展现的魅力,能够有多少可以被评委于瞬间充分捕捉到?
综观经过历届评委评选出来的优秀作品,可以发现,这些作品,既呈现了中国当代摄影发展的面目,同时也在不断定义着摄影以及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对于摄影的理想与使命。由来自世界各国的具有专业威望的评委们所评选出来的优秀作品,不是为中国当代摄影为何而设定边界,而是为了移除妨碍更深入地理解摄影与中国当代摄影的边界的束缚,以此推动有关摄影的想象,也刺激人们从这些获奖作品中展望摄影的可能性与中国当代摄影的前景。
好的制度设计能够保障评奖结果的相对公正并且具有公信力。而相对更具公信力的评奖也会因为其公正运作而吸引更多人们的参与。从这个意义上说,好的评奖是一种制度生产。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通过对于评奖过程中具体环节的创新,来为优秀作品的涌现创造条件。因此,这样的制度是具生产性的,也是有生命力的。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通过包括创设三影堂摄影奖在内的各种举措所尽力体现的,不正是这样一种想要在制度上更好地推动中国当代摄影发展的初心吗?
▷ 三影堂摄影奖的十年-摄影在 2018: 图像制造的覆变
凯伦·史密斯
上海摄影艺术中心艺术总监、西安 OCAT 美术馆艺术总监艺术史家、策展人、评论人
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
肇因于三影堂摄影奖十周年的庆祝活动,我被邀请对当下中国摄影的新发展、新特点分享一些我的看法。我能指出许多积极的发展。摄影更为广泛地出现在中国的文化景象中,我们对这些发展也越发熟悉。但是对我来说,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特点,已通过近年来的一些“紧急状况”变得具体起来。这是一个我仅能形容为关于“本质”的问题。首先,是关于我们现在在照片中看到的内容的本质,并由此涉及的影响了摄影师对选择内容的思考过程的本质。其次,是关于照片作为印刷物的材料形态的本质。此处,对于印刷流程的理解,以及那些我们称之为摄影的特性——这些定义了摄影有别于绘画的特性——似乎越发狭窄了。对这些“本质”每一种形式的忽视,威胁摄影成为一种仅仅作为图像制造的还原性实践。
当然,这些具体的关切并非显见于此次的十周年展览中。展览作品的多样性印证了那些刻画了过去几十年中国摄影领域内实践的多样性。在内容和观念上的多样之外,这些作品也反映出,摄影师、使用摄影媒介进行工作的艺术家在他们作品中所使用的各类创造性方式的技术、手法、形态、材料等。正如我们能看到这些不同个体的快照都有其风格和方法,这使我们全然意识到,好的艺术家通常不只与他们手中的工具有关:展览中摄影师们的作品正是基于直觉、意识、目光完美统一的结果。在那些被选入围三影堂摄影奖的申请者的作品中显而易见的,正是当下年轻一代的摄
影师似乎有意在探讨关于材料和形态实验的本质。换句话说,这是对这一媒介自身基础的有益发问。不难理解这一问题为何是必要的。我们常把那种同过去进行了全然切割的形式创新等同于成功。然而,想要在摄影的领域内取得这样的成功并非易事。这并非因为今天的摄影师们不够有创造性,而是因为制造照片似乎已变得容易。但毫无疑问的是,对于任何艺术形式,创作一张伟大的照片,如同创作一幅伟大的绘画,需要具备深远的目光与卓识。
另一方面,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尽管这很难用语言来唤起——与 20 世纪那些强调相机和镜头的使用的摄影师相比,许多当下的摄影师并非用同样的方式“观看”,或者说有着同样类型的目标。现今大多数相机的自动化功能使得理解如景深、光圈等摄影特性变得不再那么必要。普遍的美学的转向以及具有影响力的摄影师的作品的成功,也推动了将图片框景解构为在一个矩形内进行图像的构图(的理解)。伴随着一些美化软件如 Photoshop 的应用,这一情况也使得在框取一个主体时不再需要过多考虑“边缘”(edges)的问题。通过使用当下大部分相机技术所提供的马达驱动的功能以及使用最为昂贵的器材,摄影师们能够不假思索地轻易“快拍” (snapping)。同时,因为照片能够后续在电脑上被“制造”,摄影师也不那么需要在给定的时间内去考虑捕捉在镜框中的内容。
这种意识缺失的直接原因或许来源于当下摄影图像的普遍性,其规模即使在三影堂摄影奖创立的十年前也是不可想象的。当时在中国的摄影师远没有今天这么多。而每年不断增长的申请摄影奖的人数,以及摄影在当代文化生态中变得不可磨灭,都是对三影堂所进行的工作的明证。当下摄影所面临的挑战,不再来自摄影被公众接受为一种语言、一种艺术形式是,对我来说,它来自一种由社交媒体创造的更为广泛的社会现象。它塑造了一个不断增长的且紧张的照片生产活动的竞技场。这一活动在本质及目的上来讲是全然关于数量而非质量的。今天的技术意味着在当代世界中绝大多数拥有手机的人可以每天拍摄照片。即便他们自己没有一部智能手机,但毫无疑问他们的家庭或者亲友也是有的。即便他们自己不拍摄照片,他们也一定是别人拍摄的作为日常生活的场景以及那些特别的场合(如远足、和家人朋友的庆祝活动,或者那些在每天寻常事件中显露出的非常时刻)中的对象。
这一状况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摄影作为艺术表达或者社会记录的理解:正如作为当代形式的自拍的出现已经挑战了传统上肖像的实质。其直接结果即是我们能形容为(非常宽泛意义上的)在主流社会中前所未有的摄影民主化。所有类型的图像以与其目的、重要性、美学质量并非必然相关的各种理由得到传播。通过微信(作为最直接的例子),大多数人对于其爱好者的快照、屏幕截图或者拼合的图像已经见怪不怪;这些图像远比全职的、专业的摄影师创作的作品被更多的人看到。这里的问题并不是关于版权,甚至是浅薄艺术的美学对于传统上被认为是高级艺术的威胁,而是关于摄影图像如何在当今的世界找到它的价值。通过生产?通过冲击力?通过传播?
对于摄影师的作品以及他们“观看”和捕捉世界的视觉(带给了我们对生活和行动的方式理解的全新视角)的特定技巧来说,这种日常生活中的摄影图像的普遍性意味着什么?面对充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大量快照,摄影师们应该如何定义他们的作品?以及,如果他们选择一种融合了各种主流图像制作特征的风格,这种挪用的讽刺性该如何与它试图进行批判的图像形式加以明确区分?
在荣荣和映里构思三影堂摄影奖,以及运营一间这样的机构占据他们绝大部分的实践和创造精力之前,摄影创作是他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他们习惯使用黑白的胶片和中画幅的相机。一旦他们完成了构思中的框景,他们就回到暗房,并使用放大机制作明胶银盐照片。在某些特定系列中,他们会在放大作品后,使用百多年前已然发明的传统墨水对照片润饰以颜色。三影堂创办之时,它的一个主要功能便是与其暗房、居住空间以及工作室的环境相关的。这一项目以为前来进行驻地的艺术家提供暗房体验为主要核心。暗房还被用来进行大师课程,以及为三影堂诸多展览制作作
品——那些令人惊叹的照片就是在这里完成的。日本摄影师北野谦的作品《面孔》是我马上想到的例子。在接下来的十年之后,当我(作为上海摄影艺术中心的艺术总监)试图帮助摄影师们为我们的展览制作明胶银盐照片时,惊讶地发现暗房几乎已无迹可寻。数字技术(1990 年代末被引入相机中)已然“扫荡” 成为社会的主流。并且对于那些使用胶片负片的摄影师,以及小圈子里那些屈指可数的、拥有自己暗房设备的专家来说,数字艺术亦贬损了暗房照片的制作。我们可能还要考虑,当图像不但以数字技术被创造,且仅仅在屏幕上展示,并由此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物质性的情况下,这对摄影意味着什么?当摄影图像与计算机等建构的图像相融合的情况下,问题变成了,这张照片是什么?它是图像吗?它是作为物体的照片吗?如果它是物体,那么此物体、此照片必然是手工的吗?它的物质纹理、它的打印尺寸、它使用的油墨或纸张的质量是否还应得到重视或者有值得被讨论的价值?从本质上讲,什么是我们希望展出的作品?
或许正是这些原因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在年轻(某些案例中年纪较大)的摄影师中,对于老旧工艺(氰版照相法、湿版胶摄影以及黑白摄影和手工上色技术等)卷土重来的兴趣?其中一个具体的例子是骆丹,他花费了一年时间在中国西南偏远的地区云游,用湿版拍摄了他的《素歌》系列,该系列也使用了铂金印相工艺。还有一些人,例如蔡东东,收集、组合以及拼贴了他从二手市场上收集的黑白照片。蔡东东使用既有的照片,手工对其进行修改、操弄,以至几乎使其成为雕塑,并且在暗房中使用了重印工艺。同时,黄晓亮也建构了他的图像,但不同的是,为了使得他的照片看起来像是炭笔画或是平版印刷出来的,他以舞美师的方式在完全影棚的环境中手工制作了所有道具并塑造了灯光效果。
类似地,受到文学诗歌的启发,塔可为了找到与他为自己设定的哲学任务相契合的地点,“构建”了行旅中的图像。我们在卢彦鹏颇具氛围感的图像中能够感受到类似的诗意之地,那些图像只消一瞥就知是来自别的年代。他那些看起来颇为自然的风景是通过丰富累积的灰色影调形成的。但这种制造得来的灵晕,是在暗房中召唤的,而不能简单地通过外部世界观看到。“这就像在暗房里作画,”他曾说,“我用我的手在显影的过程中感受这些图像。”
摄影内在的一个品质,即是它能够塑造超现实之感,这一特征也能在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中被察觉到。摄影师冯立(因其在摄影领域的贡献获得了 2017 年度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发现奖)自觉地对这一特征加以展现。他的照片捕捉现实中的一瞬。尽管这些瞬间是被选择并由此建构出来的,但也仍直接指涉一个具体直接的情境——尽管这些场景被转化为凝结在时间中的某种诡异和出人意表的东西。我们可以说,冯立发掘了现实中诡谲的一面。这一现实每天与我们狭路相逢,却只有摄影能令其显现至此,让我们停下片刻,思忖图像是否真实,而生活又为何如此奇异。最终,摄影师让我们从此下意识地以不同的目光看待现实。“我唯一能告诉大家的就是我的疑问。”冯立说,“很多时候我不过是一个提问者,面对眼前所发生的一切用一个问题来回答又一个问题。答案,其实永远都是一个问号。相机,充当了我提问的工具,让我可以随时举手发问。”这就是只有摄影才能做到的事。
那么,更为年轻的摄影师们是如何通过他们的镜头看待这个世界的呢?这一问题,或许可以通过任航、罗洋、陈哲作品中的不同方式得以解答。乍一看,这些作品似乎都在处理一种既有着对于身体或心理上令人不适的亲密,又与不安和疏离保持了冷静的距离,从而牢牢把握住了他们的主题。初次看到陈哲这组令人印象深刻的获奖作品时,一定会给人不悦或者不适的感觉。你不会轻易忘记这些图像,主要原因倒不是它们达到的美学成就或者能给人带来愉悦心情。而是,它们从个人的经验到公众的意识,都与时代紧密相连,并对当下作为个体的意义进行发问。为了什么,又或者为了谁,我们每天循规蹈矩地生活,去承受挫折和无聊、孤立无援和惶惶不安时的痛彻心扉,以及得过且过地活着的麻木?罗洋和任航一样,迷恋于年轻和浪漫的事物,以及如魔法般充满玄机的性别游戏。我们会好奇,当青春的热情散场,又会有什么取代这样的迷恋?我们已经与一些人惜别,就像任航,他或许已然从某些角度为我的问题提供了答案。问题现在留给了其他人。
回到我对当下摄影的思考,展览中呈现的每一种方法表明了被视作摄影师的真切视觉。图像在被捕捉的瞬间,摄影师其心、其思、其手完美地统一起来。这一代表当下工作中的年轻摄影师群体,同样展现了摄影的新环境。在这一群体中,图像的传播更多是通过技术平台被体验到的,比如通过他们的 Instagram 和微信等。这也是关于材料的问题变得有趣的地方。对那些在模拟时代开始学习和热爱艺术的人来说,美术馆是最为直接可及的平台,但观看实际作品与审度社交媒体上传播的图像是全然不同的体验。另一个有关近来中国艺术家实践的例子,来自本次的参展艺术家蒋鹏奕。他采用的微妙材质使得作品呈现出轻盈的质感和通透性,犹如发光体一般。当这些纯粹的抽象作品以机械的方式复制于书或杂志上,抑或通过电子荧屏被看到时,会被转化为另一种扁平乃至寻常之物。它们只有被亲眼看到时,观众才能够理解作品展现的尺度以及蕴含的视觉。
技术恒常变化,一如生活习惯以及美学。因而,不论我的关注点如何(它们仿佛回溯到了久远的前本杰明时代),时代终将向前,其他的思考方式也将取代我的。然而,关于当下的摄影是什么的问题,即便是在十年后,当三影堂摄影奖来到第二十届之际,仍将是值得回溯的。总而言之,到那时,摄影又将会如何被理解呢?
▷ 三影堂摄影奖十周年
饭泽耕太郎
摄影评论家、摄影史学者、日本摄影杂志总编辑
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
我想应该是 1998 年的时候。我因为杂志工作的需要,在北京用了一周左右的时间,考察中国年轻摄影家们的动向。这期间采访了许多的摄影家,但其中印象最深的还是荣荣。他当时和张洹、马六明等人一起离开北京东村(那个上演过传奇行为表演的艺术家聚集地),来到了六里屯和朋友们一起生活。披着长发的他,眼里闪耀着光芒,描绘着中国当代摄影未来的样子,满是要开创新世界的强烈愿望。虽然当时日本的摄影现状已经很成熟了,但是相比较而言,缺乏活力且停滞不前,我只记得当时特别羡慕他有这样的热情和动力。
后来,荣荣与日本女摄影艺术家映里相遇,并于2000 年开始共同创作。他们来日本的时候我们会时常见面,我感觉到他们作品的尺寸越来越大,存在感也越来越强烈了。再后来,不知不觉间,他们已被视为中国当代摄影的代表人物,在世界各地都举办了大规模的摄影展览。2006 年的时候,听说他们要在北京郊区成立中国第一家民办摄影艺术中心。我当时真的对这种事情是否能成功持将信将疑的态度,即使到了 2007 年,收到三影堂已经成立的消息,关于这样一个机构到底能够如何运营下去,我仍没有一个很实际的感受。
2009 年 4 月,我首次拜访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三影堂摄影奖从那一年开始设立,主要是为了给能够促进中国当代摄影发展的年轻摄影师们提供展览、交流的机会,而我被邀请担任此届三影堂摄影奖的评委。我到达后感到非常震惊,三影堂的规模和活动内容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想。艺术中心园区的面积有 4500 平方米左右,展示空间估计是东京写真美术馆的两倍大。此外,还设有艺术家工作室、暗房、图书馆和艺术家驻地空间。没有国家或市政府的资助,整个机构靠以荣荣和映里为中心、几个年轻工作人员一起组成的团队来运营维持,这在日本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顿时,我的脑海中跳出了“中国梦”这几个字。
说实话,这确实是一个很棒很有野心的机构,但是我很担心它到底能够持续多长时间。但事实证明,这种预想完全是多余的。这之后,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继续稳步发展,不仅仅是三影堂摄影奖,还和法国阿尔勒国际摄影节联合策划了“草场地摄影季——阿尔勒在北京”,做了许多高质量的展览和出版工作, 2015 年还在福建省厦门市开办了分部。
值得关注的是,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还一直与日本的摄影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至今为止,在北京和厦门的三影堂举办过森山大道(2010 年、2015 年)、细江英公(2011 年)、荒木经惟(2012 年)、蜷川实花(2016 年)等人的大规模展览。还有即将到来的植田正治的展览。此外,还有许多日本摄影师、艺术家曾在摄影节期间举办个展,或在三影堂驻地创作。但在日本,目前还没有与之相应的关于中国当代摄影的展览活动或出版计划,这一点是很让人遗憾的。这可能也将成为接下来的重要课题吧。
现在,这个令我难忘的三影堂摄影奖迎来了它的十周年,我衷心地祝福它。我曾担任第一届和第二届的评委,和那时相较而言,现在的投稿人数增加了不少。看起来,这个奖项也已经成长为能够代表中国当代摄影艺术的摄影奖了。八万元的大奖奖金对于年轻艺术家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鼓励,但最棒的事情是,从第一届的大奖得主阿斗开始,新生代摄影师们开始纷纷登上这个舞台。在 1990—2000 年代,日本举办的“写真新世纪”和“3.3 平米展”(现名“1_WALL”展)之类的公募展,成为摄影师鲤鱼跃龙门的地方。而我想,三影堂摄影奖也在发挥着同样的作用。
在这十年间,当然不会只有好的事情,肯定也会有一些负面的事情。中国当代摄影仿佛在经历快速发展后慢慢进入稳定期。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也好,三影堂摄影奖也好,接下来可能会面临许多问题,但我很期待看到接下来的十年会是什么样子。或许只是绵薄之力,但我也希望能够在日本给予三影堂这份支持。
▷ 2008年以来的中国当代摄影新生代
蔡萌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部副研究员、博士艺术评论家、策展人
时光荏苒,弹指间,作为一个持续发现、关注和扶持中国本土青年摄影师和艺术家,以高水准、国际化和当代性视野进行评审的三影堂摄影奖已经十年了,它的“发明者”荣荣邀我写一篇文章,并说:“可以表扬,也可以批评。”然而,作为一个相对近距离的观察者和参与者(2015 年,我曾有幸担任过三影堂摄影奖评委,并负责初选及终评),我更愿意将视野放到过去十年间的中国当代摄影场域,将三影堂摄影奖作为一个具有指标意义的案例,去观察并分析它对该领域做出的贡献,进而就围绕它所诞生的这一代摄影 “新人”在中国当代摄影中带来的新现象、新变化,以及新价值,展开简要评析。
1976 年以来的中国当代摄影,几乎每隔十年就会诞生一批年龄在三十岁左右,表现活跃的青年人。虽然他们的人数在众多的中国摄影艺术家中,所占比例微乎其微,但恰恰是他们的作品往往领一时风气之先,并往往具有某种建构一个时代特征和水准的指标意义。比如:1980 年代的四月影会、人人影会、陕西群体、裂变群体,以及北河盟等一大批 50 后青年摄影师群体;又如:1990 年代活跃在北京前卫艺术圈的刘铮、荣荣、王庆松、洪磊、洪浩、韩磊等一批60 后青年的艺术家个体;再如:2000 年初的一批来自广东媒体的 70 后青年摄影师。那么,2008 年以后,依托于三影堂摄影奖所出现的这批出生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青年摄影师,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2008—2018 这十年间中国当代摄影的一个缩影。
长久以来,中国摄影的研究对象更多的是新闻报道、历史见证和政治宣传等,我们总是试图解读摄影文本,关注照片主题,探究图像内容和表述方式(这些固然重要),却很少关注摄影这一艺术形式本身,以及这一“形式”带来的审美特性,和这一“形式”在当代艺术中的应用。当然,我们也很少关注艺术家如何借助当代艺术这一“方法”,介入摄影,激活照片,并提供新的视角和新的可能性。但是,通过最近十年的近距离观察,我发现这批 80 后、90 后的青年艺术家已经逐渐摆脱 1990 年代观念摄影中对摄影进行“图片”化的简单认识,甚至也摆脱了对西方的“图像” 模仿。他们对西方摄影有着更为全面、系统、深刻和清晰的认识,并开始回归摄影本位。而这次回归,既不仅仅从摄影媒介特殊性入手,探讨摄影这种艺术形式的审美价值,也不完全是从一种当代性视觉外观的表层实验,去检视摄影在当代艺术中的位置及其在艺术(或美术)史中的意义,更不是简单地去探寻摄影在当代艺术语境中的位置和在现实中与其的关系。也许,这样的表述是最为贴近他们的——这一代青年摄影师对摄影的认知逐步回到“正常”(Normal),并逐步将当代艺术作为一种“方法”,将其有效接入摄影。如果说之前的几代摄影者还时常纠结于纪实摄影与观念摄影的意识形态纷争,那么新一代青年摄影师们已经打破这个藩篱,并从其中跃出,不再为自己贴上某一摄影类型的标签。如果说,之前的几代摄影师或多或少地热衷于对西方摄影的图示模仿,那么新一代摄影师们似乎更擅长用理性分析和抽象思考的方式去重新审视和处理自身与历史、现实,以及生活的关系,并已开始尝试探索自己的语言、风格和样式;如果说,上几代的摄影青年们除了创作之外,还要策划展览、搞宣言、写文章、做出版,甚至还要搭建空间和创办艺术机构的话,那么新一代青年摄影师们往往不被这些周边的琐事拖累,他们更集中精力地去思考摄影。我在这里并没有贬低摄影前辈之意,前辈们对中国摄影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值得尊敬且不可回避。但每一代人要做每一代人的事儿,时代变了,语境变了,视野和格局都变了,青年艺术家在处理他们与时代关系的过程中,自然会产生新的话语体系和可能性。
过去的十年中,随着全球化带来的高速变革,中国当代摄影的话语空间、生产机制、组织方式、评价体系、展览制度等重要方面,悄然地实现了提速和升级。在这一进程中,由展览(摄影节、摄影双年展)带动,与之伴生的摄影奖项,成为重要的“助推器”。以三影堂摄影奖为代表的几个重要摄影评选,客观上起到鼓励和促进青年摄影创作的活跃局面。他们为青年摄影师们崭露头角提供了重要平台,并激发出青年摄影师们参与的极大热情。放眼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青年摄影师有如此规模的活跃度。以三影堂摄影奖
为例,平均每届的投稿都在四百份左右。于是,我们看到很多青年摄影师通过参与这些评选活动,之后开始在国际舞台上频频亮相,更有甚者,夺得国际摄影的重要奖项,并获得海外展览、出版和驻留的机会。比如:张克纯获得法国阿尔勒发现奖,苏杰浩获得意大利布里埃尔·巴西利科摄影奖,陈哲获得玛格南基金会 Inge Morath 奖,张晓获得美国罗伯特·加纳德摄影基金,张立洁获得德国史泰德摄影书奖,任航的画册由德国塔森(TASCHEN)出版,杨圆圆获得亚洲文化协会(ACC)纽约奖助金驻留项目支持在纽约 Art in General 进行半年的驻地,等等,不一而足。之前的几代中国青年摄影师,从未有过如此多的国际机会。
在西方,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当代艺术思潮的影响下,摄影与其自身审美特性的分离就从未停止过。甚至,拉萨·史密特(Rasa Smite) 等人在2017 年策划的一个名为“数据流”(Data Drift)的展览中曾指出:“如果绘画是古典时代的艺术,摄影是现代时期的艺术,那么数据的可视化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媒介。”从一方面看,摄影这一艺术形式在今天看来已越发变得古典;但从另一方面看,它更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研究的广泛领域。在人手一部智能拍照手机和社交媒体结合而诞生的影像民主化,以及当代艺术中不断演进的数据可视化的当下,摄影越发成为一种广泛延伸、参与、介入人类日常生活的重要媒介和复杂的互文性文本,改变着人们的表达方式、交往关系、行为习惯,以及填满我们的公共和私密的生活空间。我们的年轻摄影师们在这个方向上的思考与探索,可谓与西方同步。他们虽没有太多作为参照的西方样板,或者说随着出国机会的增多,他们已经开始模糊“西方”这个概念本身,但他们有的是一种现代知识谱系和良好的中西方教育背景,以及更为开阔的国际视野和得天独厚的中国现场。众所周知,近几年出国留学学习摄影的青年人越来越多,随着他们的归国,既为中国当代摄影领域带来一股新风,又给本土摄影师们带来压力和启发。“海归” 青年摄影师对中国当代摄影的提升做出的贡献,功不可没。
而在过去的十年中,还有几个不被人察觉的现象。一是一批优秀青年女摄影师的崛起。这在三影堂摄影奖历届的入围者和获奖者中,以及各类展览中女性所占比例的提升中早已显露无遗。她们以细致缜密的情感表达、丰富多变的观看视角、理性严谨的呈现手段,以及混合着公共与私密的暧昧关系,在中国当代摄影的话语空间中发出她们的声音。而另一批强势登场的,则是摄影“川军”的异军突起。围绕成都这个舒适的现代都市工作和生活的一批摄影师,续写着中国当代摄影发展过程中的新“群体现象”,且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摄影中一道独特景观,不断完善并充实着中国当代摄影的生态系统。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在这个新人辈出的年代,我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当代摄影提速和迭代的现实,具体从每届三影堂摄影奖公布入围的名单中便可见一斑。这当中,我熟悉的摄影师名字越来越少,此一状况,近三届尤甚。当我穿梭在最近三届摄影奖展览开幕式上由越来越多年轻而又陌生面孔构成的观众当中时,越来越多 90 后开始大规模取代之前的 80 后,抢滩登陆。参展的艺术家换代了,参观的观众也换代了。似乎中国当代摄影的又一个“新时代”到来了。这让我顿觉悲欣交集,不由得唏嘘不已,感慨万千。
布尔迪厄曾说:“摄影是中产阶级的艺术。”按我的解读,这个“中产阶级”既指创作者,也指的是欣赏和接受者。当这一批 80 后、90 后成为社会主角,他们的知识结构、审美趣味、价值判断将为这个社会带来巨大的变革。当 2020 年全面小康社会即将到来的时刻,站在这个时代的交叉口上,我们有理由相信,摄影在中国将会迎来它怎样的又一个“新时代”。